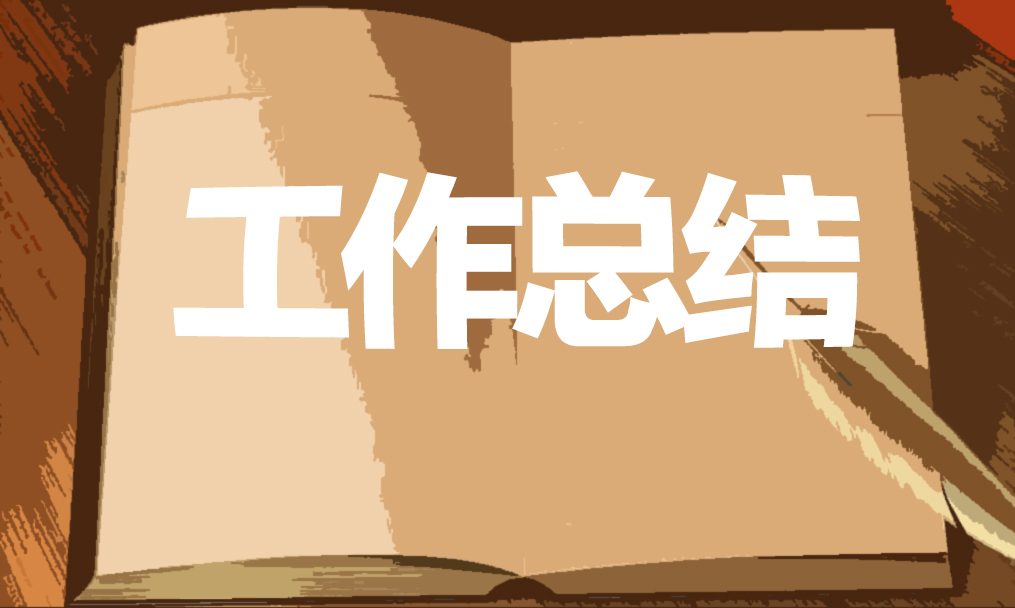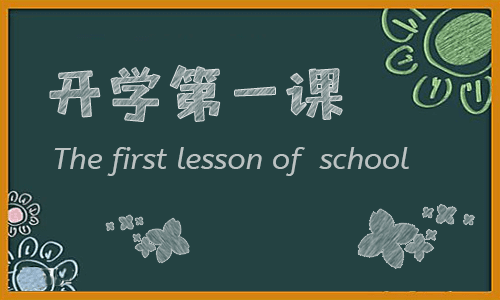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精选5篇)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以落地运河沿岸城市公益直播的形式,用镜头记录真实的城乡生活千年运河。小编在这给大家带来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精选(5篇),欢迎大家借鉴参考!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篇1
首先,大运河的开凿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创造,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时间的持续抑或是空间的延展,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出现,在沿运河带的荒野上又呈现出了具有崭新特质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运河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中国六大水系得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因大运河这根厚重的纽带而联结在一起,中国的自然水文系统相对封闭的状态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个超大的流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自然水系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其流域经过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该区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带,运河开凿前原本是地广人稀、林莽茂密、沼泽遍野,还处于半开化的状态,随着早期运河的开通,江南逐渐成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锦绣之地。
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先秦时期,作为蛮荒时代的江南还是城镇稀落,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是最繁忙的运输大动脉。两岸“行商坐市、常亦数千”,洛阳亦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使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临清,因为把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造成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跃成为明清时期“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中心城市。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因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如北京通州的张家湾,天津的河西务、杨林,浙北的乌镇、南浔等。大运河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
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运河两岸矗立的亭、桥、塔、闸、寺庙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兴。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将相的书文遗迹,诸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贽的《焚书》《藏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吴门四才子、东林党人,清代的扬州八怪等无不是与运河水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运河的通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各区域文化的交融,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岭南文化等随运河的流波而相互渗透。同时,大运河也为新技术(农耕技术、印刷术、造纸术等)的传播开辟了通道,使中华文明日显昌隆。
再次,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无论是自然生命还是人类、城市和文化生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诞生之后,也因为有了运河的养护而成长发展。虽然有人认为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劳民伤财为的是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对大运河的开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不管帝王将相的意愿如何,实际上运河开通之后客观上所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养护。一方面,运河水滋养了无数的生灵,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虾之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渔业、商贸业、造船航运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使沿岸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运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担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护着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灾害之时增添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灾害影响的屏障。以唐宋以来的江南为例,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养护,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饶,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运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粮、丝、棉等传运天下以养育生命。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篇2
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人们常赋予“中国大运河”各种不同的意象,有人说她是“中国脐带”,也有人说她是中国城市的“温床”,这些寓意都在于表达大运河对生命的创造和养护所作的贡献,正是因为大运河对其沿线自然、城市、文化生命的哺育,才使运河自身在漫长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运河儿女的勤劳智慧不断使运河呈现出新的生命气象。在当代,“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迎来了运河变化发展新的契机,在现代化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大运河因为申遗成功而实现其生命转型,她的文化生命将得到充分彰显,“活态的、线性的文化遗存”“复杂的、丰富的遗产档案馆、博物馆”是对其文化价值的高度评价,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只是运河变迁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成为世界遗产不是“中国大运河”的终极目标,保护大运河,使其“生生不息”的精神品质得到可持续发展才能体现大运河最根本的意义。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篇3
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 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篇4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佑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千年大运河文脉颂中华公益直播活动观后感篇5
“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催生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大运河的热情关注。同时也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去重新认识大运河。毫无疑问,循着运河开凿、疏浚、贯通的历史去深入具体了解大运河,考察大运河沿岸丰富的物质遗存,揭示运河对中国2000余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影响等等都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对申报世界遗产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只是我们在解读因运河而存留下来的显性的物质形态之后,不要忘却中国大运河的流波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众多物化的内容,与运河的流波一起流淌的还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精神,而这些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去总结、归纳和凝练,同时需要我们高扬一种精神。正如同奥林匹克精神以“更高、更快、更强”鞭策运动健儿奋力拼搏、勇攀高峰一样,大运河文化精神将引领我们为保护母亲河的永续流芳贡献生命的光和力。
有学者认为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表达了大运河的一种精神特质,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大运河的一种静态精神,而实际上众所周知,大运河是线性的活态的文化,是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因此,以静态的精神特质归纳大运河复杂的、动态的、多样的精神内涵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应该从运河对中国的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去追寻,我们发现,大运河自开凿之始到南北贯通,始终对中华大地上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衍生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样貌呈现出“生生不息”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动态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这既体现了中国大运河在长达2000余年历史流波中的根本特征与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理解世界的方式相融通,也符合当代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征程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生生不息”在词源上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事物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在传统文化中,儒学家们认为,生生就是变化,就是创造生命,就是生意盎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革故鼎新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本貌。《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是为“大德”。儒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大德”,就是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和成就生命。中国儒学传统的这种根本理念恰恰就是大运河文化精神的旨归。